搜索
-
×
- 首頁
-
本系簡介
-
×
-
概述
-
曆史沿革
-
機構設置
-
規章制度
-
聯系我們
-
師資隊伍
-
×
-
按職稱
-
按學科
-
教學教研
2020年7月3日上午,複旦大學向榮教授應邀在我系做題為《“黑死病”與歐洲公共衛生體系的誕生》的講座。
本次講座為菠菜技术交流论坛“大夏世界史講壇高端講座”2020年系列的第七場,講座由菠菜技术交流论坛曆史學系教授、世界曆史研究院執行院長沐濤主持。本次講座采取騰訊會議系統“雲端”視頻連線與直播,來自複旦大學、武漢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及菠菜技术交流论坛等院校近300名師生參與此次雲端講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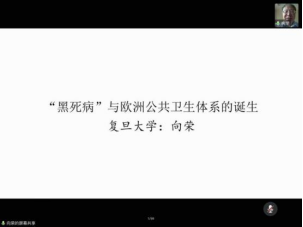

向榮教授是歐洲中世紀史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在疾病史、社會史方面造詣精深。本次講座緊分析了“黑死病”在歐洲社會的流行狀況與歐洲公共衛生體系的誕生。
講座伊始,向榮教授首先對歐洲“黑死病”進行概述:1347年至1351年,歐洲爆發了特大鼠疫“黑死病”,導緻歐洲一半左右人口的死亡,大流行之後又出現反複發作,延續到1720年—1722年的“馬賽大瘟疫”。歐洲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危機,卻并未被危機吞噬,在與“黑死病”的反複鬥争中,歐洲人擺脫了早期的恐懼,建立了公共衛生制度。
“黑死病”究竟是一種什麼病?傳統觀點認為,“黑死病”特指1347年—1351年發生在歐洲的大流行病,因其傳染性強、緻死率高而被人稱作“黑死病”。1894年法國微生物學家亞曆山大.耶爾森在香港發現了鼠疫杆菌,并提出了人類曆史上曾經曆包括14世紀歐洲“黑死病”在内的三次鼠疫大流行。腺鼠疫的臨床特征與薄伽丘和編年史家記載中“黑死病”病人的臨床特征相一緻,因此耶爾森的解釋一度被醫學界和史學界廣泛接受。
而20世紀70、80年代以來,修正派學者提出了不同觀點。英國細菌學家J.F.D.什魯斯伯裡認為:按照鼠疫病原學,“黑死病”通過黑鼠傳播,黑鼠作為家鼠,不習遷徙,傳播速度不可能快,緻死率不可能高,故“黑死病”的慘烈程度實際上是被編年史家和現代史家誇大了。他還提出,由于“黑死病”的傳播途徑是鼠—(鼠)蚤—人,而非人傳人。因此,英國封戶、封村、封鎮的措施是無效的。英國動物學家格雷厄姆·特威格則認為,黑鼠是熱帶動物,不可能大面積出現在西北歐,并據此推斷席卷歐洲的“黑死病”不是鼠疫而是炭疽。
針對修正學派的質疑,史學界也給予了回應。1994年英國史學家瑪麗.霍洛斯克依據現代醫學知識,結合“黑死病”曆史文獻,從三個層面回應了修正派的質疑:首先,她提出鼠疫并非隻有腺鼠疫一種,還包括了肺鼠疫和敗血性鼠疫,其中肺鼠疫有着明顯的人傳人特征。其次,鼠疫傳播過程中,重要的是鼠蚤而非鼠。再次,“黑死病”杆菌能夠變異,什魯斯伯裡等修正學派學者的研究基于19世紀及其以後對鼠疫的觀察,與“黑死病”時期有很大的差異。2010年,挪威史學家奧利.J.本尼迪克特出版專著,系統分析了殖民地時期印度鼠疫文獻,充分吸取跨學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對修正派學者的觀點進行了系統批判:首先,法國古微生物專家對馬賽黑死病人牙齒分析,發現了鼠疫杆菌的DNA,證明“黑死病”并非炭疽或其他。其次,動物考古學證據表明,黑鼠在羅馬共和國時期随商貿交往從東南亞傳入歐洲,并在維京時代傳入了歐洲最北部,具有較強的通過進化選擇适應新環境的能力。再次,本尼迪克特通過分析殖民地印度鼠疫研究委員會的報告,指出醫務工作者已經充分認識到鼠疫可通過多途徑跳躍短距離或長距離傳播。
向榮教授同時提出,在傳染病史研究中曆史文獻和對文獻的分析仍然是最基本的,新科學可以幫助我們澄清疫病的性質乃至傳播途徑,但是不能取代曆史文獻及其對文獻的分析。原始文獻是曾經發生過的客觀曆史的見證,是研究問題的出發點,簡單套用現有科學原理不僅會偏離曆史真實,而且也使現代科學逝去了曆史維度。因此,傳染病史研究中,史學家的介入是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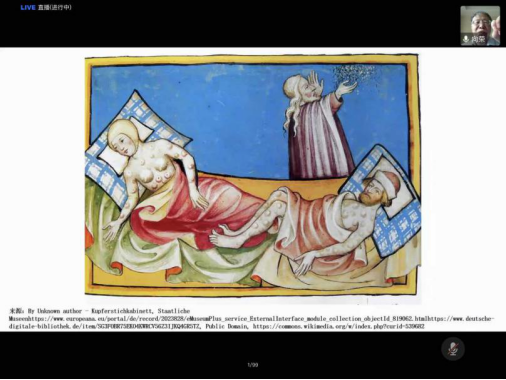
接着,向榮教授系統講述了“黑死病”時期意大利抗議鬥争與制度創新。面對空前慘烈并反複出現的“黑死病”,整個歐洲人心惶惶,亂象叢生。歐洲有組織世俗化的抗疫鬥争是從意大利開始的。這并非偶然:首先,這得益于14、15世紀意大利經濟的發達,有足夠的物質和醫療資源投入到防控鼠疫鬥争中。其次,在高度商業化的社會中,意大利人理性務實,受宗教意識形态束縛較少,意大利有着發達的基礎教育,還是中世紀大學最早出現的地方,大學教育有着很強的實用性。最後,文藝複興時期的意大利出現了不同于中世紀的新型國家。“黑死病”流行期間,意大利實施了包括隔離、建傳染病醫院、疫情通報制度、使用健康通行證、建立常設的公共衛生機構等在内的抗疫措施,并取得了顯著成效。
随後,向榮教授對英國和意大利各自的抗疫舉措進行了比較分析。英國直到1518年才在亨利八世大法官和首席國務大臣托馬斯.沃爾西的推動下開展了防疫抗疫鬥争,雖然起步晚,制度沒有意大利完善,但實際效果并不差,英國在疫情期間的人口損失遠沒有意大利嚴重,經濟仍保持着持續增長的勢頭。英國向意大利學習了包括死亡統計、疫情通報等在内的防疫舉措,但并未完全照搬意大利的經驗,同意大利相比,英**疫鬥争有自身特點。首先,不同于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意大利,16、17世紀英國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有助于在大的領土國家範圍内推行整齊劃一的防疫措施。英國政府雖未形成常設的公共衛生機構,但充分利用“國王統治下的自治”傳統,發揮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彌補了管理制度方面的缺憾。其次,英國因地制宜,并未用建立傳染病院的方式防控鼠疫傳播,而是用封戶、封村乃至封城的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再次,16世紀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對英國和意大利産生了不同影響,作為新教國家,英國主張“因信稱義”,反對羅馬天主教的迷信繁瑣儀式,堅持教會從屬國家,大大減少了宗教因素和對防疫、抗疫鬥争的幹擾。此外,經過宗教改革,英國廢除了中世紀教會的慈善救濟,建立了以濟貧稅為基礎的政府救助制度,大大提升了應對貧困和突發性災難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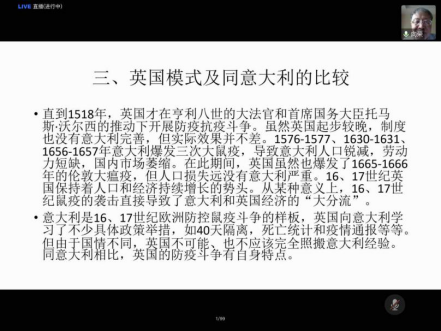
最後,向榮教授對本次講座的内容進行了總結。在與“黑死病”的反複鬥争中,歐洲人逐漸走出了早期的恐慌和非理性狀态,通過理性探索,依靠集體和國家力量,歐洲人最終戰勝了“黑死病”。意大利和英國是歐洲抗疫鬥争的典型代表:意大利是抗疫鬥争的先行者,但其完美的防疫制度并未達到人們的預期效果,既與制度本身有不切實際的因素有關,也與其他政治文化因素制約有關。英國起步較晚,但政策舉措符合國情,廣泛的社會動員彌補了制度本身的不足,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因此,向榮教授提出,完美的制度是否有效,需要放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中同其他因素結合起來考察。對史學工作者來說,回到過去的曆史場景,重視曆史本身的複雜性,避免意識形态和過度的理論構建,才更有可能接近曆史真實。向榮教授同時指出,跨學科研究不能失去曆史學特色。
講座後,向榮教授與在線師生進行了互動交流,對于學生的提問進行了詳細解答,以下摘錄了本次講座的部分問題及其回答。

對于歐同學提出的問題“歐洲黑死病的全球影響怎樣?”。向榮教授回答: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一書中的觀點是黑死病起源于中國,後傳到中亞、歐洲等地區,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但向榮教授提出,根據目前讀到的資料可以推斷,“黑死病”并非起源于中國。現在普遍認為,“黑死病”起源于亞歐大草原西部鹹海地區,向西傳播到南俄羅斯和整個地中海沿岸,造成上述地區40%—60%左右的人口死亡。歐洲是最早控制“黑死病”的地區。“黑死病”在奧斯曼帝國一直延續到19世紀才得以控制。向榮教授認為,黑死病是半全球性問題,對歐洲和中東地區的影響最大。到19世紀中葉埃及的人口還沒有恢複到“黑死病”爆發之前。
對于同學提出的問題“除了意大利北部和英國以外,其他地方是怎樣應對黑死病的?”。向榮教授指出,阿爾卑斯山以北大陸和意大利半島南部也采取過防疫措施,但大多是向意大利北部城市國家學習,采用意大利模式,但都沒有意大利北部和英國成功。在意大利16、17世紀三次大瘟疫期間,意大利南部地區如那不勒斯聘請過北部專家,也采取過一些嚴格的防疫措施。
對于同學提出的問題“怎樣做學術綜述?”。向榮教授講述了個人如何培養學術綜述能力的經曆,并向同學們提出建議,不建議将前人觀點進行簡單羅列,而是要充分理解,抓住要點,把握相關學術研究的發展趨勢。對于太厚太難讀的學術專著,若想短時間内把握基本内容和主要觀點,可以讀讀學術期刊上的書評,西方學術界很重視學術書評,書評大多評述到位。為提高效率可以采用細讀和泛讀相結合的方法,國内外的研究成果大多參差不齊,代表性論文和專著要細讀。一般來說,權威期刊和權威出版社的研究成果水平較高,要更加重視。學術史梳理很重要,真正的專家可以從你的學術史梳理判斷你的研究是否入門;更重要的是,學術史梳理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的前提。學術的生命是創新,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新問題,一篇文章寫出來總要有一點自己的觀點和感悟,不能完全人雲亦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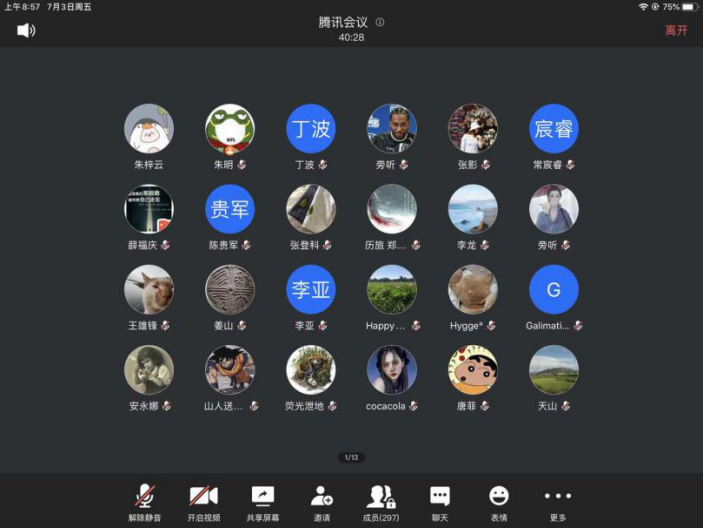
-
-





 冷戰史研究中心
冷戰史研究中心
